鳄雀鳝、罗非鱼、清道夫……愈演愈烈的鱼类入侵何时休?
中国幅员辽阔,海陆兼备,复杂多样的水环境孕育了独特生态,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间,各地鱼类入侵导致的生态困境已经愈发明显。
在2022年,河南汝州云禅湖发现两条鳄雀鳝并抽水捕捞,此后短短一月内,北京、湖南、广西、江苏、青海、宁夏、云南、山东多地相继爆出鳄雀鳝踪迹,密集的热点发酵不仅激起广泛关注,也让鱼类入侵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鳄雀鳝的大嘴
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的水系中,外来入侵鱼类已经对原生土著鱼种产生严重的生存压力,在华南、华东自然水系里,西部食蚊鱼、革胡子鲶、罗非鱼入侵规模还在扩大;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已出现多宝鱼、美国红鱼等入侵鱼类泛滥的趋势。
自上世纪以来,由于日趋严峻的全球生物入侵形势,入侵物种的传播途径研究成为热点,但在很长时间里,这些研究的重心都着眼于鸟类、植物和陆生动物(尤其是昆虫和两栖动物等)领域,而鱼类等水生生物入侵问题研究则较为冷门。
鱼类的入侵问题之所以长期被忽视,除了它们的入侵被水面掩护不易察觉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一种逻辑判断——鱼必须生活在水体中,迁移扩散受到强烈的环境限制,长距离运输活体鱼类的困难程度是远高于运输植物和陆生生物的。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逻辑基本是成立的。
根据古代典籍记录来看,从其他地区引进鱼类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来自亚洲的鲤鱼和鲫鱼在当时已经被作为经济鱼类从亚洲引入欧洲,这些外来鱼种一定也已经逃逸到野生环境中形成了入侵。
但从此开始直到欧洲中世纪时期,即便是在文化和物种交流比较频繁的亚欧大陆之间传播的鱼种,也远比其他动物少得多,更远距离的跨大陆鱼类传播几乎不存在。
然而自大航海时代之后,全球的货物和人员流动迅速增加,出于经济目的的物种引进也在这一时期快速增加,而这一时期的鱼类养殖和运输技术也获得突破。
大量的鱼类先是伴随殖民活动从欧洲引入西半球、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又进一步从殖民地回流到欧洲。
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对生物入侵的概念还处于毫无意识的阶段,对引入物种可能导致的生物入侵威胁没有足够防范,一些较为严重的鱼类入侵故事已经开始上演,尤其是在物种引入较为频繁的北美地区。
19世纪80年代前后,为了满足垂钓和商业养殖需求而引进的鲤鱼已经开始泛滥。
1892年,从德国引进的褐鳟开始直接威胁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原生鱼类玛红点鳟、金鳟。
在同一时期,罗非鱼的入侵也在亚洲出现,日本首先在本岛引进了罗非鱼进行养殖,并进一步把它作为水产良种推广到周边岛屿,这就导致了诸如奥利亚罗非鱼这样的入侵物种也在这一时期逃逸到自然水体中。
二战以后,随着全球化格局加速,大型货运飞机的普及降低了长距离运输鱼类的技术门槛,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又激发了人们对外来水产良种的需求,鱼类入侵的规模随之进入新的高峰。
以我们中国为例,1957年,莫桑比克罗非鱼经越南被引入我国,很快就出现在华南地区的水体中并野化成入侵种群,但我国对罗非鱼的引进工作还并未止步,一直到最近十几年,各地水产机构还在陆续引进和培育数十个罗非鱼新种。
1959年,邻国朝鲜赠送给黑龙江水产研究所5万粒虹鳟卵 和6000尾幼稚鱼,随后在北方冷水区域开展 养殖推广工作,不久后就有了虹鳟逃逸到自然环境中的记录。而在90年代后海水养殖进入发展期后,多宝鱼、美国红鱼的入侵也很快出现。
除了这些跨洲、跨国境的鱼类引进外,我国境内不同区域的鱼类引进同样兴盛。
上世纪60年代,云南为发展水产养殖开展了规模庞大的鱼种引进工作,先后从两广两湖引进外来鱼类34种,其中的草鱼、麦穗鱼、太湖新银鱼已经取代了当地土著鱼种成为优势种。
新疆各水系既从长江、珠江水系引进了河鲈、四大家鱼等良种,也把本地额尔齐斯河的池沼公鱼引入到吉力湖中,很快也都产生了入侵种群。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平时期的繁荣经济催生了人们对审美情趣的需求,水族业的发展也为全球范围的鱼类交流提供了更大的契机。
和水产养殖引进相比,水族业引进的鱼种不需要过多考虑品种是否稳定高效、市场是否认可等问题。
恰恰相反, “新奇”本身就是观赏鱼的重要卖点之一,不断引进更多更新奇的鱼种才符合水族业的需求。
于是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水族业引进的鱼类种类就已经超越水产养殖业几千年累积的规模。
在1900年代的北美,水族店里还只有亚洲金鱼等寥寥几种观赏鱼类可供选择,但在今天,水族爱好者可以轻松购买到数以百计的外来观赏鱼,整个北美的鱼类入侵物种中的65%已经被观赏鱼占据。
实际上,不管是水产养殖还是水族观赏的需求,本初都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合理需求。
导致其催生出鱼类入侵这一恶果的原因并不是引进鱼类本身,而是没能合理管控住这些鱼类使其进入到自然水体中。
有的鱼类被引进之处就是为了刻意投放到自然水体中的,最为典型的当属作为灭蚊防治疟疾的重要生物工具——食蚊鱼,以及作为垂钓目标鱼类引进美洲的鲤鱼。
还有的鱼类逃逸来自养殖过程中的管理不善,比如许多鱼类虽然被圈禁在网箱中,但大多数网箱都是抗风力能力特别差的老旧木结构网箱,一旦遭遇风浪等自然灾害就会导致鱼类逃逸。

繁荣的海水养殖业
1996年,我国福建引进了美国红鱼作为海水养殖的良种推广,但在2002年,厦门遭遇强台风侵袭,当地几乎全部海水网箱都发生翻覆,大量美国红鱼逃逸到海中完成逃逸
此外,养殖场直接向自然水体排水换水、人为放生丢弃鱼类到自然水体中,也是造成逃逸的重要途径。
在实际的鱼类入侵案例中,逃逸扩散的途径可能是以上多种原因的混合体。以雀鳝为例,目前可考证的资料普遍认为,几种雀鳝进入中国的时间点应该是在1990年前后。
彼时的雀鳝作为名贵观赏鱼类被引入广东的几家养殖场,随后逐渐成为国内观赏鱼市场的常客。但和很多观赏鱼一样,雀鳝经由多个渠道进入我国自然或人工水体。在2004年,温州绣山公园池塘出现一条85公分的短吻雀鳝(Lepisosteus platostomus)。根据推测,这条鱼来自于2002年该公园向广东、福建等地大批采购观赏鱼苗种时不小心混入的。
广东的东江东莞段也多次发现雀鳝幼体,除了推测是放生之外,也不排除上游养殖场换水时把鱼卵或鱼苗直接排入水体导致逃逸的可能。
不过,即便这些鱼有了逃逸到自然水体中的条件,它就一定能存活下来并完成生物入侵吗?这当然也不一定。
在我们往常的认知中,经常把入侵物种简单理解为“天赋异禀”,似乎它们的成功入侵完全是其超强适应性和高效繁殖力的结果。
在鱼类入侵领域,也确实有这样的典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规模入侵的两种食蚊鱼——西部食蚊鱼(Gambusia affinis)和东部食蚊鱼(Gambusia holbrooki)原本只是生活在美国东南部、西南部和墨西哥东北部池沼的小型鱼类,从分布区域来看似乎只适应温热带的环境。
但自从在1905年作为生物灭蚊的工具被推广到全球范围后,学者们很快就发现这两种鱼类的超凡秉性:1932年被投放到美国犹他州自然水体的西部食蚊鱼大部分被冻死,只有少数个体依靠温泉附近的暖水成功越冬。但从第二年开始,在寒冷水域也出现了安然过冬的食蚊鱼个体,到了1945年,犹他州的食蚊鱼已经完全适应了冬季的寒冷环境。
同样的故事在我国也出现过。1927年,第一批西部食蚊鱼通过马尼拉被引入上海,此后十几年还只是在江南一带水域分布。但到了1945年,天津海河的冰层下也已经有了食蚊鱼的身影。
在繁殖能力上,食蚊鱼也表现出极其高效的特性。
食蚊鱼的繁殖存在混交储精行为,雌鱼能同时储存多个雄性个体的精子,并在此后较长时间里来给自己的至少4~6批鱼卵受精,时间跨度甚至可以超过2年,这就使得食蚊鱼可以依靠很小的入侵种群就能站稳脚跟。
更极端的说,只要有一条雌性食蚊鱼逃逸,它就有可能独立繁殖后代,而且因为每批次使用的精子来自不同的雄性,它的后代基因多样性相对更丰富,能更快的跨过入侵物种的初始瓶颈期,继而迅速建立种群。
诚然,食蚊鱼这样适应性超凡的鱼类的确有更大的入侵优势,但这绝非是完成入侵的必须条件。
如果鱼类入侵的环境生物资源更充分,生态位竞争更小,那它们在新环境中的生存压力可能比原生区域还要小。在一些地理环境封闭、物种多样性较低的水域发生鱼类入侵时,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譬如位于我国塔里木盆地的特殊鱼类区系——塔里木亚区,原生鱼类只有寥寥41种,且主要是裂腹鱼类和高原鳅类,在演化过程中,塔里木亚区的土著鱼类对栖息地资源的利用方式比较单一,几乎所有的土著鱼种都是依靠下口位摄食河流底栖生物的类型,除了扁吻鱼外也没有演化出其他肉食性鱼类。
而在60年代初塔里木亚区引进鲢鱼、鳙鱼和池沼公鱼后,它们快速依靠浮游动植物站稳脚跟。草鱼、鳊鱼摄食水中丰富的水生植物资源,大银鱼则成为湖滨和上层水域的优势物种,此后引入的黑鱼、河鲈更是依靠凶悍的掠食食性捕食。
而当地的水环境类型多样,即便是对栖息地或繁殖地要求比较苛刻的鱼类,也总能在部分河段找到和故乡类似的水域,如云斑鮰的繁殖需要严格的静水区域,原本自由流淌的塔里木河本不能支撑它自然繁殖,但随后修建的多浪水库马上改变了水文环境,云斑鮰也在人为改造后的环境下成功繁殖完成了入侵。
而在这些成功安家的入侵物种挤压下,塔里木亚区土著鱼类的生存反倒面临危机——博斯腾湖的塔里木裂腹鱼被外来肉食鱼类大量掠食;池沼公鱼大量捕食水蚤类生物,直接和土著鱼类的幼鱼争夺食物;草鱼大量啃噬沉水植物,而这些植物原本是土著鱼类粘附鱼卵的重要产卵场;即便在所剩无几的水草上孵化的鱼卵,还要受到麦穗鱼、虾虎鱼等外来鱼类的直接捕食。
在近几年的调查中,塔里木亚区水系的外来入侵鱼类已经占据总鱼类物种的69.8%,土著鱼种只能依靠支流的部分河段苟延残喘,其中唯一的肉食性土著鱼种扁吻鱼,仅仅尚存一个自然种群克孜尔种群,而且这个种群几乎没有低龄鱼存在,显然是它的繁殖过程已经受到外来鱼类的严重威胁。
坦诚地说,以人类目前的手段,想要彻底清除一个地区的生物入侵,是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的。
有的时候这是个经济问题,要衡量巨大工作量和这个物种可能会带来的潜在损失之间的得失、为了清除这个物种而给原生生态带来的损失之间是否划算。
有的时候这又是个技术问题,要考虑彻底清楚它有没有技术上实现的可能。
尤其是对于水生的鱼类而言,问题就更复杂,因为光是想调查它们究竟入侵了多大区域、是否形成种群、规模又有多大都很困难。我们可以在河南汝州的人工湖里抽水捕捉鳄雀鳝,但更广阔的的天然江河、海洋中的入侵鱼类又该怎么办呢?
在生态安全领域有一个“十分之一法则”,也就是大概十分之一的入侵生物能最终扎根爆发并对当地生态带来实质性的威胁。
乍一看起这还不是个特别惊人的数字,但问题关键在于,这个基数究竟有多大?
2011年,我国环保部牵头推出了《中国生物入侵的现状与趋势》报告,里边提到一组值得玩味的数据:我国和西欧、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的国土面积差不多在一个量级上,生态环境比这些地方还要丰富多样,但当时西欧已经查出了一万多种外来生物,加拿大1442种,澳大利亚2700种,而我国缺只记录了283种。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生物入侵现状更乐观吗?恐怕不是的,这更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我们受限于调查能力和对于资金的投入。对入侵物种的调查和检测能力还很弱,还有更多已经落地生根的入侵物种没有能被察觉记录。
这1/10的入侵生物可能不是体型最大的、最凶猛的、甚至可能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生命力最强的,它们只是恰好在这片新的天地,找到了一片恰好空白的生态位,然后在长期的无人关注下默默发展起来。
所幸的是,这一局面正在改善。
2019年,国内查明的入侵物种数量已经攀升到660种。
此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生效,农业农村部也要求截止2025年要基本摸清外来入侵物种状况。
而在去年的鳄雀鳝事件后,这样的公众认识也进一步觉醒,各地的相关的摸排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
本文为科普中国·创作培育计划扶持作品
作者:任辉
审核:黄乘明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出品:中国科协科普部
监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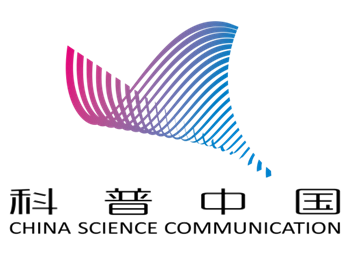
图文简介
